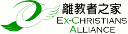| 红孩儿 2008/6/9 11:20 |
[ 本帖最後由 红孩儿 於 2008-6-9 11:22 編輯 ]
| 逆源 2008/6/9 11:28 |


 :淒涼: :淒涼: :淒涼: :淒涼:
:淒涼: :淒涼: :淒涼: :淒涼:| 抽刀斷水 2008/6/9 13:22 |

| 红孩儿 2008/6/9 17:14 |
 亡国 is more 淒涼 than we can imagine...
亡国 is more 淒涼 than we can imagine... that's why after the Tibetan Riot in March.... overseas Chinese hysterically poured out from all corners to protest against separatism....
| 红孩儿 2008/6/9 17:20 |
不知当年鸦片战争战败,香港是不是跟伊拉克一样 ....
| 抽刀斷水 2008/6/10 20:18 |
| 红孩儿 2008/6/11 03:37 |
 My Dad always chanted : 耶稣爱世人, 世人爱奶粉.... My primary school was across the street from Kowloon 邓镜波中学.... That school was huge and the Catholic fathers over there always handed out free soda and free candies to attract little kids from my primary school to go to their church to listen to their bullshits....
My Dad always chanted : 耶稣爱世人, 世人爱奶粉.... My primary school was across the street from Kowloon 邓镜波中学.... That school was huge and the Catholic fathers over there always handed out free soda and free candies to attract little kids from my primary school to go to their church to listen to their bullshits.... 
| 逆源 2008/6/11 05:53 |
[ 本帖最後由 逆源 於 2008-6-11 05:54 編輯 ]
| 红孩儿 2008/6/11 07:34 |
========================
 他们这样做,动机不只是传教那么简单, 他们也是在制造伊拉克的穆斯林和伊拉克基督徒的内部矛盾,穆斯林会感到因为他们的国家被摧毁消亡, 因此基督教的美军可以随便侮辱穆斯林: 继用枪射击他们的可兰经之后和现在又用士兵派圣经, 派有用阿拉伯语写的圣经诗句的硬币。伊拉克的穆斯林和伊拉克基督徒越是互相不信任, 越是互相攻击, 越是分裂, 美国(和以色列)就越是渔人得利...
他们这样做,动机不只是传教那么简单, 他们也是在制造伊拉克的穆斯林和伊拉克基督徒的内部矛盾,穆斯林会感到因为他们的国家被摧毁消亡, 因此基督教的美军可以随便侮辱穆斯林: 继用枪射击他们的可兰经之后和现在又用士兵派圣经, 派有用阿拉伯语写的圣经诗句的硬币。伊拉克的穆斯林和伊拉克基督徒越是互相不信任, 越是互相攻击, 越是分裂, 美国(和以色列)就越是渔人得利...[ 本帖最後由 红孩儿 於 2008-6-11 07:37 編輯 ]
| 红孩儿 2008/6/13 08:45 |
戴学稷
伯驾(PeterParker,1804-1888),亦译作巴驾或派克。美国传教士、医生兼外交官。他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于1834年6月1日在纽约长老会教堂被任命为传教医生,10月受美国基督教差会美部会的派遗来广州,成为基督教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医生。
1835年11月4日在广州新豆栏街租赁房屋设立眼科医院(时人称为“新豆栏医局”)企图通过为广州人民诊疗疾病“以博取人民的信任”来进行传教活动。
伯驾的眼科医院“由于浩官(十三行总商伍秉鉴、伍崇曜父子——引者)和奥立芬(美广州同孚洋行老板)的慷慨捐助,这个医院有了稳固的基础,而且成为永久性的医院”①。1838年2月21日在英国鸦片贩卖的大本营东印度公司的支持和建议下,“中华医药传教会”在广州成立,东印度公司哥利支医生任会长,伯驾任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等人都是终身董事,同年4月,由哥利支、伯驾和裨治文三人联名签署一份该会的“宣言”,声称他们将努力于“有助于推倒偏见和长期以来所抱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以此来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
而公然供认他们的目的是:第一、将医学科学“移植于中国可能产生有益(于他们)的效果;第二、是“将可以从这个方法搜集情报,这将对传教士和商人都有极高的价值”②。
1839年秋,林则徐在广州期间曾因疝气病间接托人请伯驾开诊疗药方。而在这之前的当年7月间,林还曾派行商送去瓦特尔的《各国律例》一书中若干段落,请伯驾翻译为中文,“摘译的段落包括战争及其附带的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等”,同时要他“对有关鸦片的情况提出事实的陈述,并开列出鸦片受害者的一般性药方”,此外还垂询了有关他所办的眼科医局的情况③。
伯驾是美国早期那些主张利用鸦片战争的有利时机派遣海军到中国进行示威,乘机取得侵华权益的鼓吹者之一,而且是美国传教士中最积极的突出代表。在鸦片战争期间,伯驾特地回国活动。1841年1月伯驾赴华盛顿拜访当时任美国总统的凡·勃俊(MarinVanBuren)和国务卿福西瑟,旋被转荐去会见新的国务卿韦伯斯特和新政权的其他人物,伯驾向他们提出,要求“立即派遣全权公使迳驻道光的宫廷”。
以后又再度拜访了新总统约翰泰勒 (JohnTyler)和国务卿韦伯斯特。直至1842年9月,他还在策动曾任美国总统的亚达姆斯(JohnQuincyAdams)作为美国的专使来华 ④。当年11月伯驾从美国返抵广州,又鼓吹说南京条约签订后已有“足够的证据可证明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⑤,催促美国政府迅速派代表团前来中国乘机渔利。
正是由于伯驾等美国传教士与在华商人的鼓动和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给他们带来的“兴奋”,美国政府认为“如果要想获得与英国相等的利益”就必须派遣专使来华与清政府进行谈判。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便有1843年夏天以顾盛为专使的来华。
在1844年7月签订中美《望厦条约》的过程中,伯驾不仅作为顾盛的译员之一,而且为顾盛当谋士,出了不少主意,成为顾盛使华的重要助手。
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于1844年起参加当时还设在广州的美国驻华使馆中工作,1845年至1855年任美国驻华使馆头等参赞,其间三次代理公使职务,1855—1857年正式任美国驻华公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他与英法俄各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竭力扩大对华侵略权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华时,他又主张美国出兵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岛。1857年8月伯驾卸任回国,1879年后在美国任《中国医务传教会》会长。
伯驾作为一名传教医生,是美国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代表人物之一。鸦片战争后他继续在广州借行医传教进行侵略活动,颇不受当地人民的欢迎。道光二十六年五月(1846年7月)和七月(9月),广州人民曾连续贴出揭帖,针对伯驾欺压中国人民的事实,谴责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为“夷人奴才”,屈从于伯驾的压力扣押不肯出租房屋给伯驾的老百姓的媚外行为,指出伯驾“倚恃官势押逼,必要赁与居住,方肯罢手”和在代理公使职务期间“輙敢窃权恃势,狐假虎威,随处生波,骚扰民居”的霸道行径,以致形成“至今舆情不协,街众弗容”,使得“我等绅耆士庶军民,虽三尺孩童,无不深恨其滋扰,佥谓彼既随处挑衅,与其贻害于将来,孰若歼除于早日”不可调和的严重局势。
为此,广东绅民准备行动起来,向伯驾的侵略行为进行清算,特地给了他警告⑥。由此可见伯驾尽管打着“慈善”、“为人医病”的招牌,他在广州依然是不得人心的。伯驾作为一名美国侵华的急先锋,他的名字与美国早期文化侵华活动是分不开的。
①〔美〕赖德烈著、陈郁译:《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商务印书馆,第89、96页。
②以上转引自顾长声:《传教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2一45页。
③参看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6一46页;并转见张劲草:《林则徐—中国近代杰出的国际法学家》,载福建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林则徐与鸦片战争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④〔美〕赖德烈著、陈郁译:《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商务印书馆,第124—125页。
⑤同上,第116页。
⑥《官府辱国殃民贴》、《为狡夷肆扰贴》,见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下册,古籍出版社,第787—788页。
"《鸦片战争人物传》"
http://baike.baidu.com/view/247764.html
| 红孩儿 2008/6/13 08:55 |
在鸦片战争以前和鸦片战争期间的外国传教士中,美国的传教士也不甘后人,他们在帝国主义早期的文化侵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在广州及其他地区进行了不少活动,并把他们的活动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的军事进攻的政治、经济侵略密切结合起来。这里着重介绍其中两个人:裨治文和伯驾。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一1861),美国基督教美部会(后改称公理会)教士。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826年大学毕业后到神学院进修,1829年 9月自神学院毕业就接受美部会的聘请为该会派赴中国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
他由美商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资助,免费乘坐他的商船并住在他在广州的商行里。他接受美部会的指示,到中国向“那众多的人民”传播“福音”,并要求他就有关中国社会的各种状况向差会作详尽的报告。
裨治文于1829年10月14日自纽约上船,经过一百三十五天的航程,于1830年2月15日到达广州。当时在广州的外国传教士只有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一人。
在裨治文自美国出发前差会就要求他特别向马礼逊求教,因而裨治文到广州就跟马礼逊学习汉语文。
随后由马礼逊倡议,裨治文任主编,广州美商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提供经费和印刷场所,于1832年5月起出版一份英文的月刊,名为“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文译作:《中国丛报》,又译作《中国文库》,旧译作《澳门月报》(与林则徐编译的《澳门月报》无关)①。自此开始,至1851 年12月约十年间《中国丛报》共出版二十卷(每月一期,每年一卷,其间1839年5月迁澳门,1844年10月迁香港,不久又迁回广州。)登载了鸦片战争前后二十年期间有关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字、风俗……等方面的调查资料,其中包括了中外关系和外国人在中国活动等情况,也包括了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等中国官吏的政策措施活动等记载。
其间1833年来华的另一名美国教士卫三畏也参加了编辑的工作。裨治文等在他们主持编辑的《中国丛报》上,在鸦片战争前几年间,不间断地进行战争煽动,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的舆论,叫嚣:对中国“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提出的使用武力迫使中国订立一项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认为:“采用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必将一无所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并公然不讳地承认“我们是主张采用有力的果断措施的鼓吹者”。他们并就中国的军事实力进行情报调查,作出了结论说:从军事角度看,中国实不堪一击②。
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在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同时,对英国大量走私鸦片的罪恶勾当从来不加指责,他们在中国所搜集的各种情报为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他们所制造的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舆论,所提出的谋划和主意对于英美等国政策起了很大的影响,因而他们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
作为传教士和《中国丛报》的主编,裨治文是林则徐所注意的在广州的外国人之一。
1839年6月虎门销烟时,裨治文和美国商人经氏以及舰长弁逊等十余个外国人曾乘舰由澳门前往参观。
当时裨治文等是抱着怀疑态度前去抓把柄的,认为“中国人是不会销毁一斤鸦片的”或者“大部分鸦片一定会被偷去” ③。
但在事实面前他们不能不承认“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为忠实的了。”
经过实地观察,他们的结论是:“即使偷窃一点鸦片,那也要冒极大的生命危险。最低限度,这令我不得不相信了。”④当裨治文等前去参观时,林则徐在销烟现场接见了裨治文,同他讨论了致书女王等问题,并向他表示想得到地图、地理书和其他外文书籍,特别是想得到一部马礼逊编的英华字典⑤。
裨治文在参观虎门销烟后也把自己的观感写成了一篇《镇口销烟记》的报导,刊载在《中国丛报》上。
裨治文在鼓吹以武力手段打开中国门户的舆论上不遗余力,并主张传教士应不顾中国的法律深入内地活动,1843-1844年,美国派遣专使顾盛来华逼订《中美望厦条约》时,他与另一名美国传教士伯驾任顾盛的秘书兼译员。
1847年,他迁往上海,除传教外,并从事上海外国人的公众事务,1857— 1859年任上海亚洲文会会长,1861年死于上海。著有《广州市及其商业介绍》(1834 年,广州)等书。北京贝满女校最初是他妻子裨爱利莎在他死后于1864年创办的。
①参考吴乾兑、陈匡时《林译<澳门月报>及其它》,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②以上均转引自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第1章。)
③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165页。
④同上,第169页。
⑤前引《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吴、陈文。
"《鸦片战争人物传》"
[ 本帖最後由 红孩儿 於 2008-6-13 08:57 編輯 ]
| 红孩儿 2008/6/13 09:07 |
在英国对华进行鸦片走私和鸦片战争前后的侵略活动中,西方传教士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和他的儿子马儒翰以及德籍传教士郭士立等人先后都服务于英国侵略东方大本营的东印度公司,与英国侵略者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传教士来到中国,用他们自己的话:“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
他们利用传教的方便,研习中国的语言文字,熟悉各地的风俗习惯,不仅在贩卖鸦片、外交谈判中充当推销员和翻译官,而且搜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报资料,为英国侵华活动出谋画策,起着急先锋和狗头军师的恶劣作用。以下着重介绍马礼逊父子和郭士立的有关情况。
郭士立(KarlFriedrichAngustGutzlaff)(英文名Charles,Gutzlaff1803一1851),亦译作:郭实腊、郭施拉。德国人。1823年毕业于柏林仁涅克传道学院,随又进入荷兰鲁特丹荷兰传道学院学习,曾于1824年赴英,向是时返国的马礼逊牧师表示以后愿到中国传教。
1827年毕业后为荷兰传道会派往爪哇传教。1828年脱离该会,进行自由传教①。1831年(道光十一年)来中国,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上海等地贩卖鸦片,并通过散发《圣经》和药品从事间牒情报工作。会讲普通话和福建、广东方言,能够“象一个中国人”一样地在中国人当中活动。他从1831年到1838年间,曾到中国沿海侦察至少有十次②。
1831年6月3日郭士立第一次乘坐一艘中国商船从暹罗(今泰国)出发,沿途经过福建、浙江、山东,直至天津对中国沿海进行了仔细的侦察,一路上刺探了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情报,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返回广东,在澳门上岸后受到马礼逊的欢迎和接待。他的侦察立即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所注意③。
1832年(道光十二年),在郭士立侦察报告的“鼓舞”下,英国侵略东方的大本营东印度公司广州办事处派遣阿美士德号船化名胡夏米号,聘请郭士立对中国沿海进行再一次的详细侦察航行。
郭士立化名甲利,充当翻译和医生,与另外两名英国侵略分子礼士(阿美士德号的船长)、林赛(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改名胡夏米,冒充该号船主)三人一同乘该船于1832年2月26日(道光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自澳门出发。同船七十八人,沿途经南澳岛、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和威海卫等地,复折往朝鲜、琉球,于同年9月4日(八月初十日)返抵澳门。
他们沿途借为人治病,进行传教,散发《英吉利人品国事略说》、《戒赌博》、《戒谎言》等小册子来收买人心,希求消除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不信任和疑惧心理,而其主要目的是测量河道和海湾,绘制航海图,侦察地形,调查沿海沿江一带重要口岸上清军的设防等,以便拟订一项军事侵略方案,作为英军制定作战计划的依据。
在这次侦查航行中,郭士立特别卖力。他通过调查,了解到清朝的腐败与虚实,竭力怂恿英国政府使用武力,替英国商人达到在上海和其他口岸开埠的目的。他写道:“不恐吓那个衰弱和可鄙的政府(指清政府)而采取商议的办法,将会得不到任何结果。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英国的)战舰。”④
1833年,郭士立又乘船北上销售鸦片烟士。他一边进行鸦片走私,一边向中国人传教,把卖大烟和传教紧密地结合起来,既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又摧残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在这以后,他又从事文化侵略活动,曾主持刊行《东西洋每月统纪传》⑤,并与其英国妻子温施娣于1834年夏在澳门设立一个女校⑥。
《东西洋每月统纪传》先在广州出版,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以后迁至新加坡编辑发行。郭士立及其妻在澳门所办的女校,第二年 (1835年)附设马礼逊学校,为我国早期第一个取得留美和留英大学学位的容闳和黄宽等接受西方知识启蒙的学校⑦。
1839年(道光十九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郭士立即已作为翻译随同义律辗转往返广州、澳门各地。
1840年战争正式爆发后,他随英国侵略军北上,任翻译兼情报官。这年7月5日英军攻占定海,他被任为民政长官(“舟山总督”)。
1841年英军再次北犯,他又充任翻译官与向导沿途张贴布告,勒索财物。宁波被占后,他又任宁波民政长官。
1842年改任镇江民政长官。在南京条约谈判中,郭士立是英方三个翻译之一,南京条约的中文草稿即出于他的手笔。他已成为英国侵华的忠实工具,是璞鼎查的得力助手。
1843年6月,璞鼎查任香港总督,8月底马儒翰病死,郭士立继任港督中文秘书及翻译官的职务,前后达八年之久,直至1851年死。
1847年郭士立在香港设立“汉会”(又称“福汉会”)雇用中国人到内地散发宗教传单。
1849年他曾返欧,在英、荷、德、俄、瑞典、奥、意等国演讲,大肆宣扬其耶稣化中国的计划,但没有得到什么反应。著述有英文六十一篇(部)、德文七篇、荷文五篇、日文两篇、逻罗文一篇,慕尼黑大学有其全部中文著作。关于中国近代的著作有《中国简史》
(1834年)、《1831、1832、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日记,附逻罗、朝鲜、琉球介绍》 (1834年)、《道光皇帝传》(1852年)、《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两卷本,1838年)等。
(戴学稷)
①李志刚:《容闳与近代中国》,香港版,第61页。
②③参看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9—30页。
④转引自南木:《鸦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侦查活动》,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111页。
⑤参看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68页。
⑥详见李志刚:《容闳与近代中国》,第60-65页。
⑦容闳:《西学东游记》,中译本,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章。
"《鸦片战争人物传》"
| 红孩儿 2008/6/13 09:12 |
 I believe that the Morrison Hill Road in Hong Kong was named after this bastard or his son !
I believe that the Morrison Hill Road in Hong Kong was named after this bastard or his son !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东印度公司的中文译员——马礼逊
在英国对华进行鸦片走私和鸦片战争前后的侵略活动中,西方传教士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和他的儿子马儒翰以及德籍传教士郭士立等人先后都服务于英国侵略东方大本营的东印度公司,与英国侵略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些传教士来到中国,用他们自己的话:“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
他们利用传教的方便,研习中国的语言文字,熟悉各地的风俗习惯,不仅在贩卖鸦片、外交谈判中充当推销员和翻译官,而且搜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报资料,为英国侵华活动出谋画策,起着急先锋和狗头军师的恶劣作用。以下着重介绍马礼逊父子和郭士立的有关情况。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出身较贫苦,1804年5月向伦敦布道会报名,自愿为国外宣教师,随即被送进宣教学院接受十四个月的训练。
1807年1月8日被授为牧师,1月31日被派遣来中国。他于1月31日从伦敦出发,三个月后到达美国纽约,在美国政府的协助下,搭乘美国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的三叉号鸦片走私船,绕道南美洲经太平洋先到澳门,当年(嘉庆十二年)9月7日到达广州①。
马礼逊抵达中国时年方二十五岁,遵照伦敦会的指示,他努力学习中国语文,仿效中国生活方式,1809年起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办事处(在广州十三行英国商馆)任职,年俸五百英镑②,并与东印度公司一位高级职员的女儿结婚。
他除充当汉文翻译外,并行医传教。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闭关政策,禁绝传教士进入中国,在此后的七、八年间他便以马来半岛西岸的马六甲为据点进行文化侵略活动。
他利用马六甲海上交通方便又有大量华侨聚居的有利条件,抓紧研究中国典籍,加深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先后编辑出版《汉语语法》、《华英字典》、《广东省土话字汇》,翻译并出版《新约全书》、《新旧约全书》等书。
他不仅是西方传教士中将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完整地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而且在编辑汉英文字与语法辞典上投下了大量的劳动。他编辑的《华英字典》共六卷,四开大本,四千五百九十五页,仅从《康熙字典》收进的汉字加以英译就达四万余字。
用心可谓良苦。
1815年他在另一传教士米怜的协助下,在马六甲出版一份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这是由外国人创办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个汉文近代报刊。1824年他回国一年余,由于他带回秘密收集的大批中国书籍,受到英国国王乔治四世的嘉奖并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7月,英国派特使阿美士德来中国,到北京觑见皇帝,马礼逊任汉文翻译随行同到北京。这个使团和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的目的一样,是企图减轻清政府对广州贸易的限制,取得在广州以外各地贸易的自由和驻使北京等,其实际目的更在于扩大鸦片输入。这些目的当然没有实现,但作为翻译的马礼逊却被东印度公司的经理,称为“此行的主要人物”①,他在一路上显得十分活跃。
1833年(道光十三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成立,第二年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来华。马礼逊在中国的活动受到英国政府的重视,英国国王特任命他为律劳卑的中文秘书兼翻译官,“年俸一千三百英镑,可以穿上副领事的制服,缀上皇家的领扣”,随同律劳卑与清方交涉。
在律劳卑与广东大吏的交涉和争执中,“马礼逊做了许多翻译的工作”,为律劳卑出谋画策,向广东地方官吏施加压力,进行挑衅。但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病,于8月1日死于广州③。
马礼逊是西方殖民者基督教(新教)教会派来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长时期任东印度公司的中文译员,前后任职达二十五年之久。他曾多次建议英国政府在中国自设法庭,以取得治外法权。他以宗教为掩护,进行了许多文化侵略活动,参加了英国对华的外交谈判,把宗教、政治与文化教育揉在一起,为英国侵略中国效劳。
他还积极支助美国传教士来华进行活动。他来华后的传教和文化活动,为英、美等列强在鸦片战争后侵略中国开辟了道路。
(戴学稷)
①清洁理著,费佩德译:《马礼逊小传》,广学会出版,第11页,第21一43页。
②以后增加为年俸一千英镑。
③《马礼逊小传》,第70—71页。
④同上,第155页。
⑤夏燮:《中西纪事》,卷8,第4—5页。
⑥散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第5册,第2409—2549页怡良与伊里布有关折、片。
⑦同上,第2718页。
⑧转引自郑天挺:《马礼逊父子》,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58页。
⑨李志刚:《容闳与近代中国》,香港版,第61页。
⑩④参看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9—30页。
⑾转引自南木:《鸦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侦查活动》,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111页。
⑿参看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68页。
⒀详见李志刚:《容闳与近代中国》,第60-65页。
⒁容闳:《西学东游记》,中译本,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章。
"《鸦片战争人物传》"
[ 本帖最後由 红孩儿 於 2008-6-13 09:18 編輯 ]
| 红孩儿 2008/6/13 09:17 |
马儒翰(JohnRobertMorrison,1814-1843),英国人。传教士马礼逊的长子,一般中国史籍上称为小马礼逊或秧 (young)马礼逊,出生于澳门。
他在英国受短时期教育后到马六甲英华书院进修。自幼习汉文,对中国语言文字和社会风习很是谙熟。
1830年(道光十年)十六岁时就在广州为英国商人作翻译。
1832年编成《英华行名录》,1833年著《中国商务指南》。1834年马礼逊死后他继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中文秘书兼翻译官。
他除热心传教事务,遵其父遗命修改《圣经》汉译本,与传教士麦都思、郭士立、裨治文等合作完成了新的译本,但却以更多的精力参加英国侵华的政治活动。
1839年(道光十九年)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中英交涉日繁,英方文件大多由马儒翰经手翻译。
鸦片战争爆发后,他随同懿律、义律直接参加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担任情报的翻译工作,其中包括参与义律与琦善1840年(道光二十年)7月大沽口的谈判和1841年1月迫订《穿鼻草约》的谈判以及 1842年8月(道光二十二年七月)璞鼎查与耆英、伊里布等签订的南京条约的全过程。
在战争进行时,他为璞鼎查出谋画策,干了不少坏事,例如在英军进入长江口后他知道长江沿岸清军没有设防,两江总督牛鉴庸儒腐败无作战决心,所以驱轮深入。到了京口,他又勾结扬州汉奸江寿民挟兵索贿六十万两白银,到了南京,他又声言要入城就食,索取饷糈三百万两。
在南京,一切谈判主要由他“来往传说”时常以谩语相恫吓,表现极为恶劣①。南京条约签订后,他又同璞鼎查到定海、厦门等地,横生枝节,借台湾爱国军民抗英事件进行讹诈②。
由于他侵华有功,战后他被任命为香港立法行政委员会委员兼香港殖民政府秘书。
1843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初五日),马儒翰因疟疾死于香港③。
香港总督璞鼎查为英国侵略者丧失了一个侵华的急先锋和得力干将而深感惋惜,认为这是他们“国家的一大灾难”④。由此也说明了马礼逊父子在英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初期的重要性。
(戴学稷)
①《马礼逊小传》,第155页。
②夏燮:《中西纪事》,卷8,第4—5页。
③散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第5册,第2409—2549页怡良与伊里布有关折、片。
④同上,第2718页。
"《鸦片战争人物传》"
| 红孩儿 2008/6/14 08:38 |
http://libproject.hkbu.edu.hk/trsimage/christian/er00106m.pdf
| 抽刀斷水 2008/6/14 15:09 |
原帖由 红孩儿 於 2008-6-13 09:12 發表
I believe that the Morrison Hill Road in Hong Kong was named after this bastard or his son !
推測正確: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1%A9%E5%88%A9%E8%87%A3%E5%B1%B1

| 口琴王 2008/6/14 19:25 |
该有多好
| 红孩儿 2008/6/15 04:04 |
 "港耻"山道,
"港耻"山道, "国耻"游泳池,
"国耻"游泳池,  "港耻"工业学院......
"港耻"工业学院......| 红孩儿 2008/6/15 04:13 |


 "重回汉唐"干什么?
"重回汉唐"干什么? 
| 红孩儿 2008/6/15 04:59 |
 国家应视以国防安全的角度去考虑教育,医疗, 文娱及慈善事业....
国家应视以国防安全的角度去考虑教育,医疗, 文娱及慈善事业....政府要争取得到对教育,医疗, 文娱及慈善事业的 100% 控制权才可以威胁到耶教在我国的生存空间...
....耶教机构不会请个拜佛的来做CEO, 香港的政府职位空缺为什么要开放给耶教徒呢?

| 逆源 2008/6/15 05:59 |